简介
林洪桐
娄际成,王春子,张伟欣
剧情片
大陆
-1
儿童片由于其特殊的表现对象和观众层次,是一个很难驾驭的电影类型。一般来说,儿童片可分为三种:1.拍给低龄儿童看,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兴趣为主导,大多带有超现实的童话色彩。2.以儿童作为表现媒介来传达成人对世界的感受,虽然视角仍是儿童的,但其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是童真、童趣,而是现实中一些有着深刻意味的事件,观众的定位也是成人化的,比较典型的如前苏联影片《自己去看》。3.从儿童和成人两个方面同时切入并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呈现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同的主观世界。《多梦时节》属于第三种。这部影片保持了林洪桐导演的一贯的艺术探索风格,相当成功地在儿童的世界中化入了成人的话题,在儿童片领域进行了新的开拓。就叙事层面而言,《多梦时节》相当清晰描绘了两个不同的心理时空。一个是儿童的世界,充满着少男少女们的烂漫天真,年少轻狂,所使用手法基本上是写意的。特别是群体出现时,如罗菲和她的同学们在观象台上的对话段落,在红色的夕阳背景中,孩子们或坐或站,三五成群,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为一句歌词而手舞足蹈……画面构图活泼,色彩饱满,摄影机位多变,几乎没有静止镜头,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孩子们所特有的多变追求和对时代的独特感受,充满着涌动的青春活力。特别是烛光晚会一场戏,使用了非常主观化的红色滤光镜,配合孩子们对自己的作品充满幻想的解说,使整个段落洋溢着和谐浪漫的温馨诗意。另一个是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无奈的成人世界。在这一部分中,影片的描述手法是写实的。影片以罗菲的妈妈为核心,讲述了一个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夫妻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这是《多梦时节》的情节主线:原本还是比较平静的家庭生活突然被从美国回来的罗菲母亲的初恋情人华光打乱了,整个现实世界的平衡支点因华光的到来受到冲击。首先是罗菲的姥姥因不满意至今仍默默无闻的女婿而颇有微词,其次是罗医生因凭空预感到自己的威严与地位受到威胁而生抱怨,最后是罗菲的妈妈因丈夫反常的反应而产生的烦躁。这一切都没有逃脱他们的女儿罗菲的眼中,她在颇感困惑的同时把无名的怒火发泄到华光这个“外来的入侵者”的身上。因此,影片中的成人世界便成为一个有着各种尴尬无奈的让人迷惑的世界。在影像风格的设计上与儿童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在罗菲的家庭戏中,尤其是在她的父母出现在一个画面中时,大多构图是不规则的、随意的和散漫的,影调也偏于冷峻,使观众能相当直接地感悟到创作者对成人(或现实)世界的看法。影片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矛盾的解决方式并不是武断的、硬性强制的,而是自由选择、自主判断式的。在影片的最后一个叙事片段中,罗菲与爸爸坐在红艳的霞光里,探讨着人生的出路,虽然没有明确答案,但这些画面本身就成了最好的回答。相当清楚的是,在影片复杂的表意结构中蕴含着一个核心的概念,那就是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围绕这一点,影片象征性地用三代人体现三套不同而又相互影响的价值体系。首先表现的是中年人的价值观念,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观也就是社会的主流观念。影片确立了一个用以平衡的支点,这就是罗菲的妈妈。首先,她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者,特别是在男人称雄的建筑设计行业,这一点完全可以值得自豪和受人青睐。其次,她同时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性。这两点,似乎能够确保她以个人身份对于男性做出价值判断的权威性。以这样一个才貌双全、明显被理想化了的女性为价值判断的裁判者,至少从感情上是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与此相应是她的两个追求者,一是罗健刚,昔日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今日“无所作为”的牙科主治大夫。二是华光,昔日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今日留洋归国声名显赫的艺术大师。把这两人加以比较是有意思的。这两个男人,昔日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都是所在专业的明日之星,但是,只是由于在以后岁月里的不同选择和不同际遇,而造成了今日大相径庭的处境。罗健刚在国内真诚地信奉“为人民服务”的信条,几十年如一日以病人为上帝,把家中无数次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当做神圣使命的召唤。作为一名医生,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劳模”式人物,他的价值观是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宣扬的标准,也是新时期很多普通老百姓希望永远存在于别人身上的品质(但是,对于自己是否应当具有,很多人甚至抱有相当鄙视的态度)。也许正是这种相当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造成了罗健刚的现实尴尬。例如,他只是因没有发表一篇属于自己的抄抄写写就成的论文而无法得到一个早就该得到的承认,面对女儿的一句疑问,他言不由衷地说出的一句话“上辈说我们是孵不出鸡的蛋,下辈说我们是下不了蛋的鸡”,其实正是其内心相当迷茫的真实写照。价值标准的更新使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出现了断层。华光在影片中是一个虚写的人物,对于他前史的交待也是虚拟化的。我们只是通过影片人物的转述才知道,很久以前他曾去国外深造并学到了大提琴(一种典型的西洋乐器,而不是古筝之类的民族乐器)的演奏精粹(当然这其中肯定有个人的才华和辛勤汗水的付出)。但富于戏剧性的是,他此番是为了记忆中的初恋情人,而专程回国举行个人演奏会的,而且是一下子便引起了轰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显然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那种典型的名利双收的“明星”式的人物。人们的顶礼膜拜客观上更加确定了他的价值定位。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可以满足个人欲望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虽然缺乏现实根基但却有着明确历史渊源的价值观念。对于这样两种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念,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评判。影片借助罗菲的母亲的特殊位置给出了一个坚定而又是宽容的裁断。她与两个男人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只不过一个是实写,一个是虚写。影片揭示矛盾的速度相当快捷。在表现家庭生活的第一场戏中,夫妻就进行了一场相当有意思的关于“意思”对话。“你什么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那我也没什么意思”。这决不能理解为两个人的文字游戏,而应该理解成一种非常微妙的暗示。罗菲母亲的无名焦虑也许是由来已久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罗健刚并没有进入周围人们所期待的轨迹而成为一代名医,他仅仅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牙科大夫。她自己的成就感在不断攀升的同时,也就越来越不能容忍丈夫对名利的漠不关心了。特别是华光的重新闯入,使罗健刚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参照物之后,罗菲母亲的焦躁终于浮出水面,使她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矛盾心理。影片一方面通过逼女儿学小提琴(不是大提琴)来暗示她对华光价值的承认,另一方面通过与丈夫的争吵来暗示她对罗健刚人格的承认。也许正是这种心态,使得罗菲母亲的一句有些生硬的台词“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会选罗健刚”具有了现实的合理的因素。在这里,我们看到,创作者非常聪明地偷换了概念,把价值判断更替为道德判断,从而使得似乎有些倾斜的个人世界仍能维持其原有的平衡。在影片中,罗菲姥姥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也是非常市侩的。她是那种典型的(不能做出任何独立判断的)随波逐流式人物。她在影片中惟一的功能就是作为罗菲的反向参照系。从罗菲的角度如何看待现实中的(或父母间的)矛盾,这是整部影片最不好把握,而又最不能回避的问题。影片给出了一个有些中庸的而又可能是惟一正确的回答。它没有正面提出答案本身,而只是细腻地演示了罗菲心理成长的历程。罗菲从对母亲的反叛(她当面拒绝继续学习小提琴)到对母亲的心理认同(对着镜子模仿母亲照片上的各种姿势,渴望成为一个像妈妈一样的成功者),从对父亲怒其不争的埋怨(回家后对父亲的哭诉和指责)到对父亲内心世界的体察和谅解(父女同时靠墙的倒立和湖边晚霞中的对话),从对华光的敌意排斥(用口香糖弹射广告宣传画)到对华光的善意接纳(在楼梯上的并排而坐)。罗菲终于从一个感性的起点达到了一个理性的终点,把所有的一切都融合成一个独特的价值系统。作为整部影片中出现的三套价值系统的一个顶点,罗菲的结论有点似是而非:“孵不出鸡的蛋我就吃了,不下蛋的鸡我就杀了”。那然后呢?……罗菲无法回答,她只是在宁静而又甜美的梦中微笑。“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影片借用孩子们的口,道出了生活的真谛。影片中出现的极为风格化的五次梦境完全可以看成是导演艺术个性的充分体现。由于五次梦境游离了故事主线,使一些普通观众似乎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这五次梦境游离了故事主线,从而使得它的表意功能得到强化。那挂满白色鸟笼的大树,树前芳草茵茵的绿地,和煦温暖的阳光,耳语般轻柔的话音……这些美妙的视听形象充分地展示了孩子们对自然、和谐与美丽的追求,它构成了一条暗线,与主线并立存在,并在整部影片的意蕴上形成了呼应的格局,使得整部影片的内涵更加丰厚、饱满。
@《多梦时节》相关推荐
-
 HD
HD
人兽杂交
艾德里安·布洛迪,萨拉·波莉,德尔菲娜·尚内亚克,BrandonMcGibbon,SimonaMaicanescu,大卫·休莱特,AbigailChu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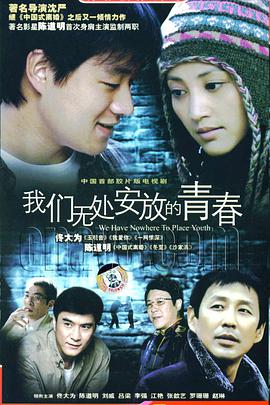 全24集
全24集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陈道明,佟大为,江一燕,张歆艺,罗珊珊,朱雨辰,冯鹏,赵子琪,宫晓瑄,余皑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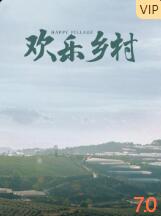 HD国语
HD国语
欢乐乡村
王嘉禾,谢雨欣,吴广林
-

等待玛丽
邦妮·阿甘,内德·阿夫里尔-斯内尔,J·伊利亚·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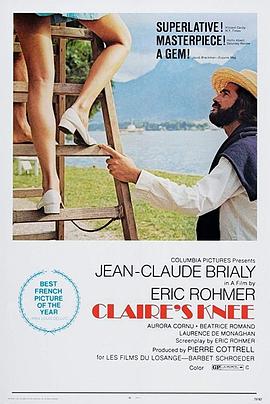 更新HD中字
更新HD中字
克莱尔的膝盖
内详
-

哈吉特
尤哈·韦约宁,萨穆里·埃德尔曼,提穆·莱蒂拉,卡莱维·哈波贾,阿图·卡普莱宁
-
已完结 共10集
临床犯罪学者火村英生的推理
斋藤工,洼田正孝,优香,山本美月,槙田雄司,清水一希,堀口ひかる,松永渚,小野寺晃良,松泽一之,生濑胜久,夏木真理